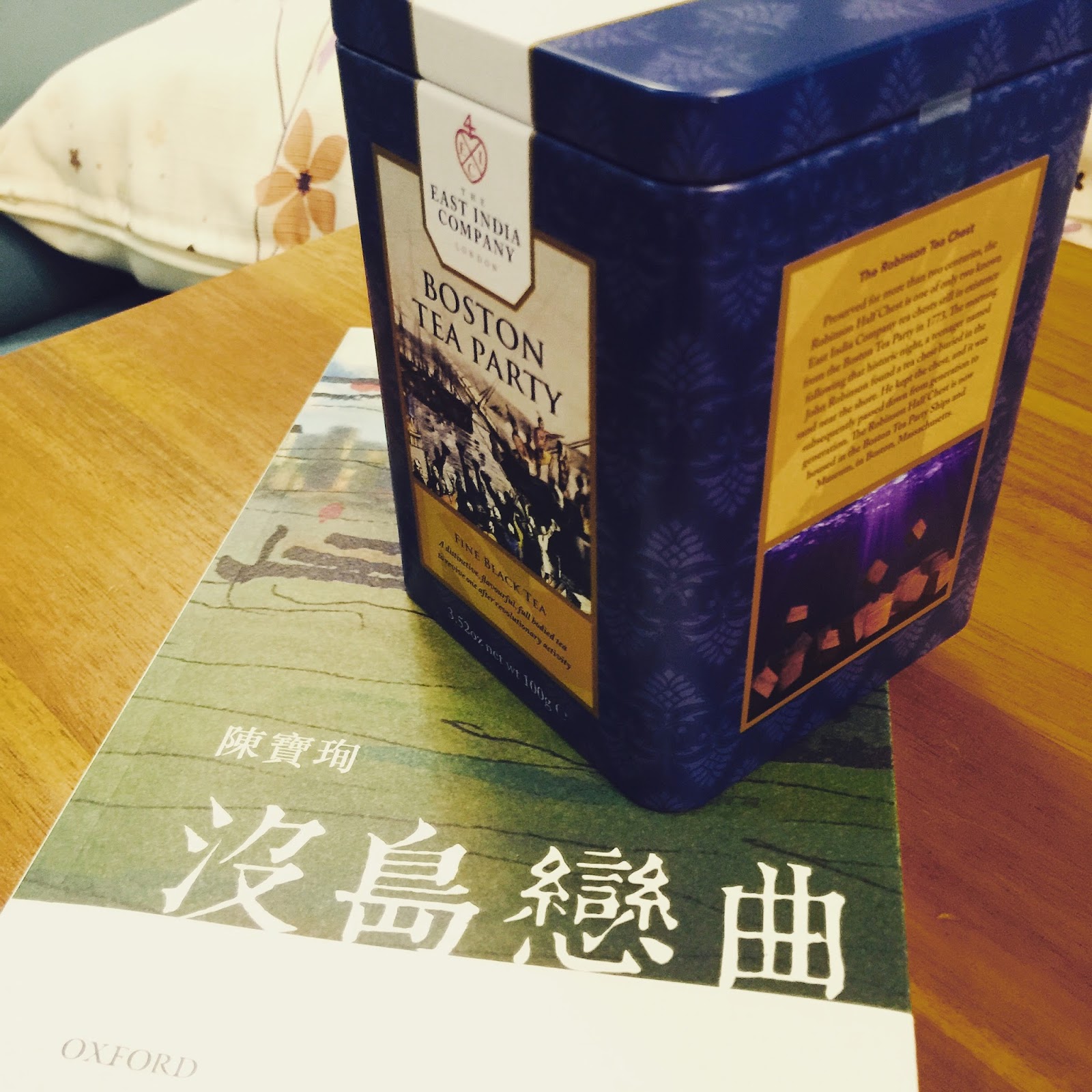首先讓你猜猜,有個國家,每年都在喊經濟不景氣,政府為了刺激經濟,想了很多方式想要扭轉經濟的頹勢,政府試過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給,利率低到近乎於0,依舊沒辦法有效刺激內需,心一橫,再試試看讓貨幣大幅貶值吧?這個國家的工業產品還算優良,增加出口促進外銷。國內投資不振怎麼辦?政府來帶動,政府舉債投資吧,反正利率是0,公債到期只要能夠繼續發新債還舊債就好......可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怎麼還不見起色呢?攤開經濟結構一看,各種官商勾結、貪污腐敗,集團企業規模越來越大,富可敵國,獲利創新高的同時,勞工的薪資水準卻不斷下降,但是隨著貨幣供給攀升,國內資產價格不斷膨漲,房價屢創新高,年輕人望房興嘆的同時,生育率也減少,這個國家終於步入老年化社會,老年人把持了經濟跟權力......問題一籮筐,國內外的專家都提出許多解方,國民卻越發無所適從。
如果不看本篇文章的標題,你會猜想這是哪個國家呢?這個國家現在是日本,未來也可能是台灣、是中國、是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這也是作者 William Pesek 破題時就點出的,全世界都害怕日本化,中文書名《手術台上的日本》描述的是日本的現況,但英文書名《Japanization》則是點出了西方人的憂慮。
日本失落的二十年的成因與起源說法有很多,撇開陰謀論不談,多半是以美日「廣場協議」伊始,日本步入失落的十年、二十年,而現在看來即將三十年,而以日本馬首是瞻的亞洲諸國,近年也因各種因素逐漸步入日本的後塵。日本失落的三十年,除了在民生經濟上對日本國民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外,某種程度也狠狠地打了凱因斯學派經濟學一巴掌,總體經濟理論在這個地方彷彿都無效了。
這本書在我看來是2010年後,西方人對日本問題的一個總結,是帶有西方人主觀意識的看法,這並不是說作者 William Pesek 講的沒有道理,也不是說日本在地觀點比較正確,而是我認為這問題已經沈痾將近三十年,各方都有各方的觀點與道理,但卻似乎沒有真正能救亡圖存,逆轉頹勢的有效方法,彷彿是手術台上的病人,找了十幾科的醫生大會診,各自開藥方,抗生素打了兩輪,肚子上剛開的刀才縫合,現在換腦外科上場。作為一個台灣的讀者,其實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去研究起源或是針對現況去提出建議或藥方,其實好奇的是,這段時間裡,日本發生了哪些事?政府的舉措是哪些?哪些做錯了?哪些又做對了?畢竟,難道你不覺得本文首段裡描述的情境,某種程度很像是台灣社會?然後你再看看三十年前、強盛時期的日本,是不是很像今天的中國?中國會不會重蹈覆轍?
先從現象開始講起。
《手》書從金融業開始講起,1997年間,成立將近百年的山一證券宣告破產,被視為是日本政府接受奧地利經濟學說「破壞性創造」的象徵,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對於金融業採取「護航制度」(Convoy System),由大銀行保護弱小的銀行,寧可讓大銀行承受、吸收合併一些中小型的銀行,也不會輕易讓銀行倒閉,銀行是日本經濟的安全防護網(想想《半澤直樹》跟劇中主人翁賦予自己的使命感),政府對銀行紓困,銀行就繼續讓企業生存,這是不是很耳熟能詳呢?記得台灣曾有所謂的「三挺政策」嗎?(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員工)
可是這樣的施政方針到底帶來了什麼後果?書中提到 Brian Reading 出版的《即將崩潰的日本》(Japan: The Coming Collapse)提及的鐵三角關係:由政客、官僚、大企業所組成的「聯盟」,每一方為了金錢而交換好處。由於實體經濟並沒有多大的增長,於是這些組織轉向財務操作獲取利潤與報酬,他們運用「財術」(Zaitech)到處投機炒作,炒作的結果是標的資產增值、公司利潤大增,更有誘因進一步操作財務槓桿,作者下了一個結論:「財務 + 技術 = 爛帳」。
再加上零利率的金融環境,這些政客、商人,對於容易取得的低利貸款上癮,貪得無饜的他們還會要求更多,幾近零利率的銀行資金提供了財團零成本的資金,而日本人高度的儲蓄率,則源源不絕的奉上扼殺人民自己的彈藥,憤世嫉俗的 William Pesek 用了一個可能是金融業內人士才比較有共鳴的低 pH 值比喻:伊斯蘭銀行。
William Pesek 是這麼說的:
『全世界的銀行體系都伊斯蘭化,而且難以回頭。伊斯蘭法禁止貸款或存款算利息,還蓋好龐大的基礎建設,協助包括波斯灣石油大亨這樣的客戶。日本央行、聯準會,與其他中央銀行提供無息的貸款,是不是有點剽竊的意味?美國總統尼克森於1971年回應傅利曼(按:應該是 Milton Friedman),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諷刺話:「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到了2009年,我們已經都變成伊斯蘭銀行家。』